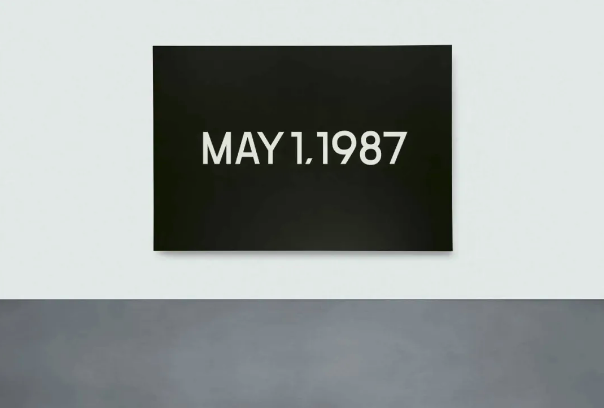前言:本展「第三維度」,如展名所喻示的,多以非二維平面畫作的立體類雕塑和裝置作品為主。親自擔綱策展人的彼得布蘭特(Peter Brant),從他近半世紀以來的收藏之中,精選出20位與他身處同世代的藝術家,包括有:David Altmejd, Carl Andre, Jean-Michel Basquiat, Maurizio Cattelan, John Chamberlain, Urs Fischer, Dan Flavin, Mike Kelley, Karen Kilimnik, Glenn Ligon, Nate Lowman, Adam McEwen, Cady Noland, Claes Oldenburg, Richard Prince, Rob Pruitt, Jason Rhoades, David Salle, Kenny Scharf, Julian Schnabel, Josh Smith, Dash Snow, Oscar Tuazon, Andy Warhol, Franz West。40件展出藏品被錯落有致地分佈在四個樓層,包跨前衛的雕塑、巨型的裝置和少數的油畫作品。「第三維度」布蘭特沒按風格或時間順序排列,而是根據視覺關係將作品進行分組,創造藝術家與藝術家之間的「對話」,每個層樓都有著鮮明不同的主題。
在紐約布蘭特基金會觀展動線很特殊。有點像是進戲院看劇,在一樓櫃檯購票、領票後,便直接被工作人員引導至電梯口,直登大樓的最高層。抵達四樓,陽光隨著電梯門的敞開而湧入眼中,光線從預期外的敞開天井撒下。接應陽光的是卡爾·安德烈(Carl Andre, 1935)標識性雕塑作品〈作為場所的雕塑〉(Sculpture as place, 1966)。(對安德烈作品不熟悉的人可能尚未「看到」藝術品。地板上排列的方整鋼板,即是藝術家的雕塑作品。)

地面上是極簡藝術家卡爾‧安德烈(Carl Andre, 1935)標識性雕塑作品〈作為場所的雕塑〉(Sculpture as place, 1966),與之比鄰的是,牆面上,非裔美籍藝術家格倫‧利根(Glenn Ligon, 1960) 的燈裝裝置 〈溫暖又寬廣的光芒〉 (Warm Broad Glow, 2005) 。
安德烈的作品看來既簡單又純粹,但事實上深藏著很深的內涵和意義。選用「不用雕」的材料創作雕塑的卡爾·安德烈,在作品上沒有一絲多餘的人為介入。與其說他將手感和創作痕跡降到最低,倒不如說他以「材料支撐概念」的大原則,對傳統定義下雕塑的技術、題材和位置進行挑戰。什麼意思呢?更白話而言,一般來說,雕塑作品都是放置在台座上,就好比畫作上的畫框,又或是在同展場內安迪沃荷用可樂空瓶創作的翻模作品,此舉是為了「將藝術和生活空間區隔開而附加的」。
而以「極簡主義」(minimalism)重新定義當代雕塑的卡爾·安德烈(Carl Andre, 1935),他卻將材料直接放置在地板上。以最簡單的直線邏輯延展,讓鋼板們並肩排列,赤裸裸地展示著材料最原始的模樣。在此,藝術家是為了將作品以更為自然、不突兀的融入至空間內。讓我們既可以觀賞作品,更可以打破虛與實空間的限制,達到日常生活融入藝術的境界。換句話說,這即是藝術家所主張的讓觀者與藝術品「自然的共處一室」,他將觀展者所產生的共鳴和經驗通通收編成為他作品的一部分。
花了點時間讓眼睛適應明亮的光線後,發現天花板是特別選用了與地板相同的木材,天與地兩相呼應,創造了一種奇特的空間氛圍,好像隨時可被翻轉的顛倒世界…當視線好不容易從地面上的安德烈拔起,向上望去,映入眼簾的是非裔美籍藝術家格倫·利根(Glenn Ligon, 1960) 的裝置作品 〈溫暖又寬廣的光芒〉 (Warm Broad Glow, 2005) 。矛盾的是,利用霓虹燈管流暢寫著”negro sunshine”的作品,沒有大小寫之分或使用標點符號,單單用打字機般的字體的〈溫暖又寬廣的光芒〉,有著如此明亮的名稱,字面上的”negro sunshine”卻是直譯為「黑鬼陽光」,引人深思。 〈溫暖又寬廣的光芒〉巧妙的被安排懸掛在天井之下,望著「黑鬼陽光」被猛烈的陽光掩蓋,正以它近乎日光燈的幽微「聲量」,轉瞬之間,發現自己正重「讀」著那歷史未能結算的慘痛篇章。

在同展廳的左手邊,我們可以看到難得一見的珍品。首次向世人展出的——掛在牆上的白色軟雕塑——《軟付費電話(幽靈版)》(Soft Pay-Telephone (Ghost Version), 1963) 出自於克萊斯·奧爾登堡(Claes Oldenburg, 1929)之手老。現年91歲的奧爾登堡為少數仍在世,並持續進行創作的波普藝術耆老。與此呼應的是安迪‧沃荷的〈布里洛肥皂盒〉(Brillo Soap Pads Box, 1964)、〈金寶蕃茄汁盒 〉(Campbell’s Tomato Juice Box, 1964)、〈Del Monte水蜜桃盒〉(Del Monte Peach Halves, 1964)、〈亨氏蕃茄醬盒〉(Heinz Tomato Ketchup Box, 1964)和〈家樂氏玉米片盒〉(Kellogg’s Cornflakes Box, 1964)。
提到瑞典藝術家克拉斯·歐登伯格,腦海浮現的畫面想必是他標誌性的大型公共雕塑作品。歐登伯格的公共藝術作品多與妻子布魯根(Coosje van Bruggen)共同創作,他們把日常生活中一件件看似毫不起眼的物件放大,親切易懂的主題、造型又幽默討喜,深得老老少少們的喜愛。然而,這樣的歐登伯格事實上是以繪畫開始他的創作生涯的。
1956年,當歐登伯格從芝加哥搬到紐約,原本希望以畫家的身分闖出名聲,卻在幾年後的一檔展覽之中改變了心意,從此走上雕塑創作之路。「1958年,我仍在創作如馬奈一般的繪畫。同時,我也嘗試做了一些『變質』的東西。後來在我發現,唯有製作前所未見的雕塑才能顛覆那個時代的藝術。自此,我就再也沒有提起畫筆做畫了。」歐登伯格開創了20世紀最大膽又具爭議性的一批雕塑作品,改變了雕塑的可能性。
且讓我補充何謂歐登伯格所說的「那個時代的藝術」。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時正是紐約藝術景象轉變的年代,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日漸衰微,許多藝術家開始進行跨領域的嘗試,如與舞者或導演合作,創作偶發(happenings)等藝術作品。而萌芽於五零年代中後期的波普藝術,事實上,是率先由一群自稱為「獨立團體」 (Independent Group)的英國前衛藝術家、「粗野主義」(Brutalism) 建築師和評論家所發起。「獨立團體」企圖透過年輕的美國文化改變階級森嚴、傳統而陳腐的封建政治體制,提出了「藝術具有當下性,而不是高於當下性,藝術應具有民主性,而非菁英主義」的新思潮,反其道而行利用美國的流行消費文化產物,揶揄現代主義以來陳腐的歐洲文化所推「永恆的」「高級藝術」。
隨著1964年,美國資深藏家李歐·卡斯特里的領軍之下,大批紐約波普藝術(New York School of Pop Art)湧入歐洲,同年的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金獅獎首次獎落美國藝術家 ——羅伯特・勞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 ——的手中,不但重新改寫了過去兩百年來美國與歐洲不對等的關係、消弭歐美文化地位之間的差距,更開始連結北美洲與歐洲的藝術場景。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波普藝術濃縮了一個時代的消費文化特徵。當半個世紀之前,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元氣大傷的歐洲普遍瀰漫著悲觀的情緒,知識份子、藝術家們開始反思現代文明科技帶給人類的災難,而遠離主戰場的美國,經濟迅速蓬勃發展,不僅正式取代了- 老牌資本主義國家 – 英國的地位,生活形態受傳播媒介(如電視、印刷業)的急速發展所影響,藝術品的生產方式亦在這樣的情境下,緊挨著消費主義與大眾流行文化 (Popular Culture) 轉型。這一內涵與現代主義運動(如野獸派、浪漫主義、抽象表現主義等)強調自我表現截然不同,普普將藝術家的自我退縮到可有可無的地位,取材多是採用最通俗、日常卻對現代生活具有重要影響的生活題材,例如可口可樂、瑪莉蓮夢露、暢通商品的商標等,把每日充斥我們感官的日常生活,以中立的、毫無表情的方式拼貼再現。
波普藝術打破了藝術創作中長久以來的高低之分、瓦解了藝術中隱含的權力及階級作用力、表現了庶民文化等特質。尤其是「絕對客觀主義」(objetive)的中立立場為識別波普藝術的重要內涵。藝術家們對於他們使用的表現對象,並不帶任何情緒,不稱讚亦不貶抑,僅僅是冷漠無情的表達。普普藝術因擁有上述種種具影響力的創作方式,讓藝術發展方向產生了”質”的改變,因此,在二十世紀的藝術史上,與立體主義具有相同重要的地位。
文 / 呂家鎔 Kayo Lu
全文刊登於亞洲藝術新聞8月刊 《KAYO藝事錄》轉載請註明出處